读书笔记(五)《中国关键七问》【简介&序言】

“ 宪法明言“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不过中国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中国农民没有农会,工农阶级在党内党外均说不上任何领导角色和政治意义。它的体制自许“具有中国特色”,不跟随既有的任何发展模式;不过除了维护党国官僚集团(以及周围的附庸)的独占地位之外,你很难说这套体制还相信什么、追求什么、还有什么理想与向往 。”——钱永详
(摘录自《中国关键七问:忧思者的访谈》序言)
书籍简介

编者:陈宜中
出版日期:2013/06/07
ISBN:9789570841916
出版社:聯經出版
关于陈宜中
陈宜中,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暨政治思想研究专题中心执行长,兼任《思想》季刊编辑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思潮、应用政治哲学,著有《中国关键七问》、《当代正义论辩》、《中国转型六问》。
部分论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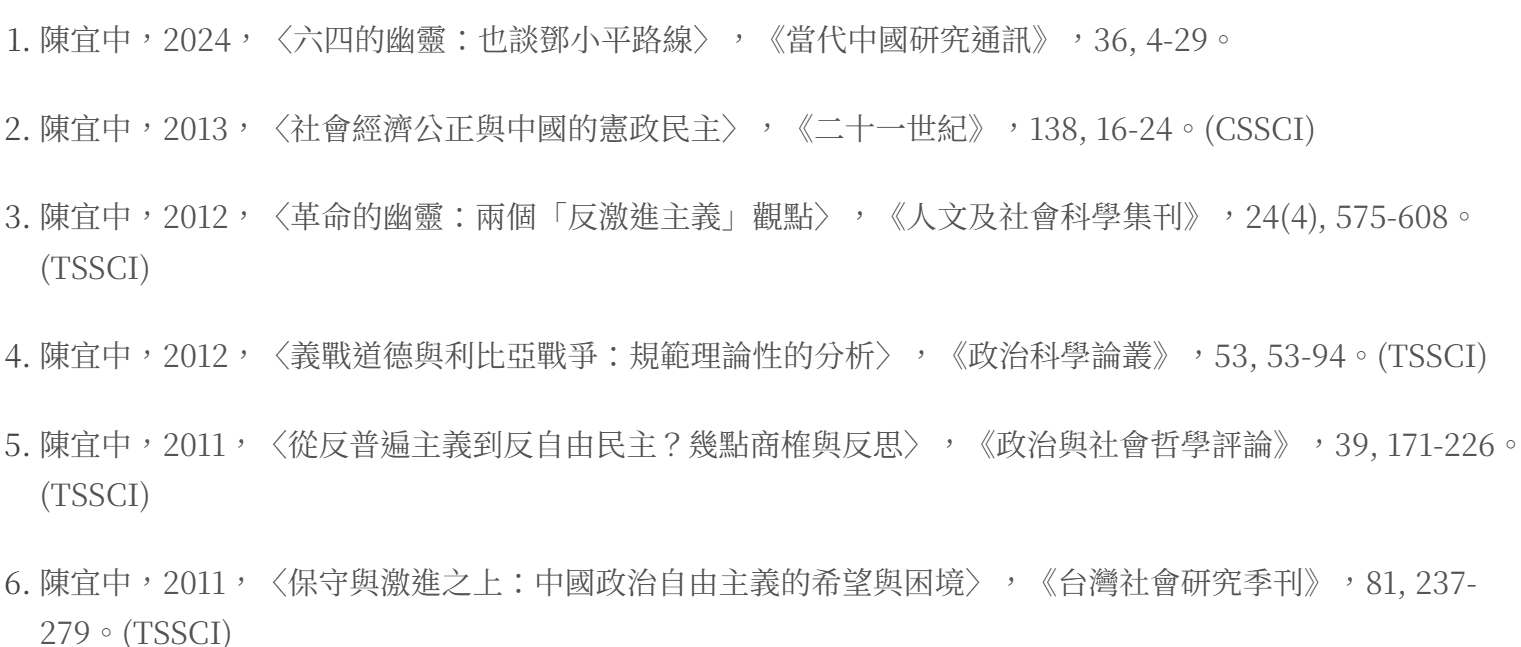
思想杂志上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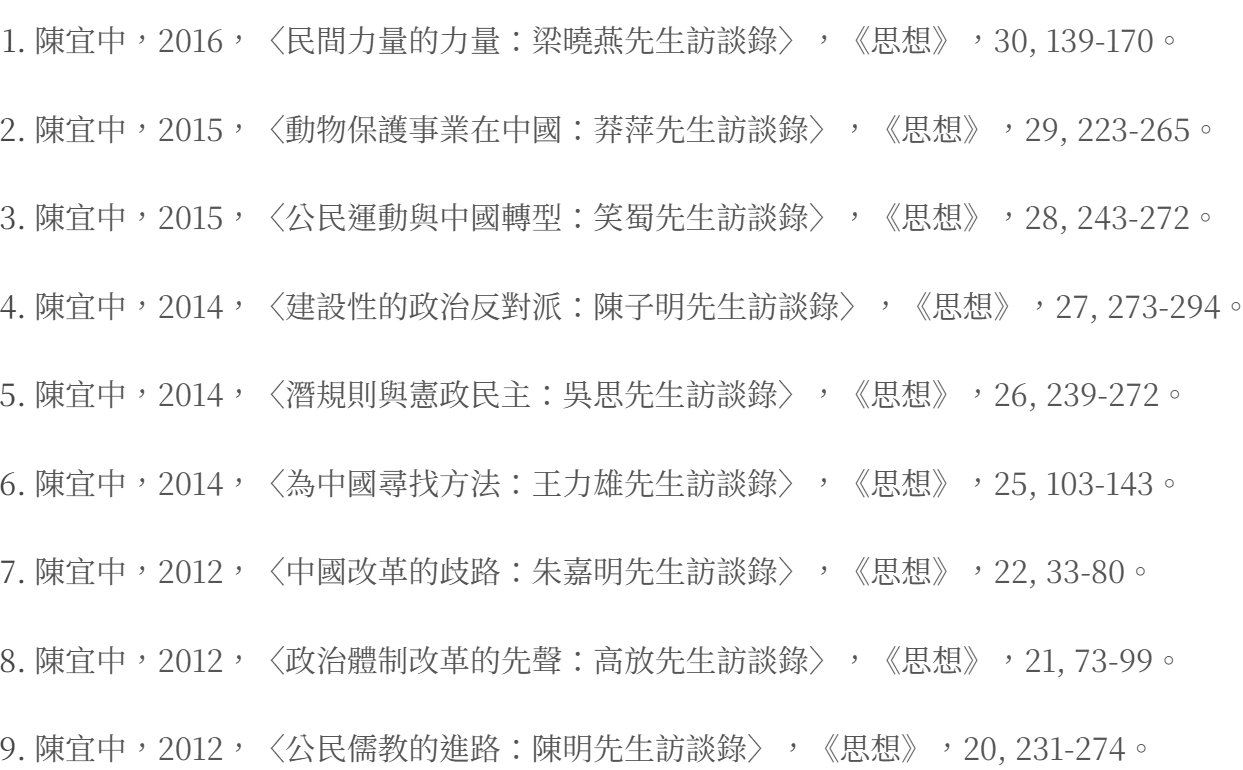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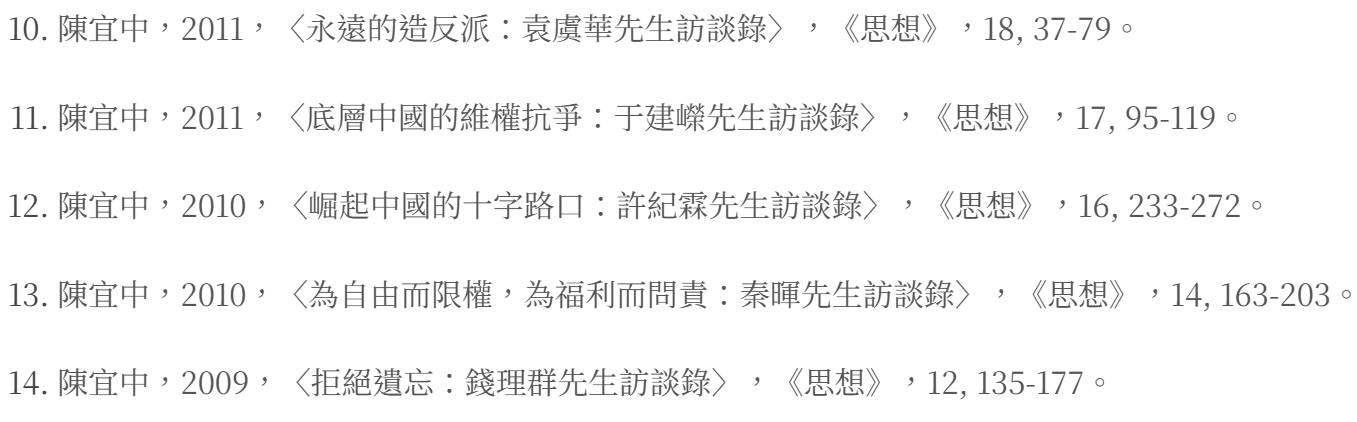
关于钱永详
生平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黑格尔哲学、政治哲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1949年,钱永祥出生于兰州。后随国民党军官父亲赴台,生长在眷村。
1965年,进入建国中学读高中,与马英九是同学,期间受到殷海光影响,接受了自由主义。
他后来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就学期间被查出私藏有马恩列斯毛著作,被记大过处分,随后被“请喝茶”、被带往警备总司令部关押6天。
1971年大三时参加过保钓运动。
1975年赴英国利兹大学深造,期间受到英国新左派影响,结识了托派人物王凡西。
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对文革感到幻灭。1982年回台,没有取得学位,后供职于中央研究院至今。
1988年创建《思想》杂志,当时只办了一期,2006年复刊,由联经出版。
政治立场
钱永祥被视为左翼自由主义者。[2]他自称感情上跟国民党很疏离,没什么好感,但肯定国民党在台湾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3]
关于《思想》期刊
《思想》是联经出版的一份以书代刊的杂志,创刊人和现任总编辑是钱永祥。其内容均为中文学者原创,1年出版3至4期,类似于季刊,每期探讨不同主题。[1]《思想》旨在团结华人世界知识分子,办一份严肃的中文思想性刊物,既非学报,也非新闻刊物,而是以学人的知识为资源,展开公共议题的讨论。

内容简介
价值重建、社会公正、文明崛起、维权抗争、毛式民主、公民儒教、体制改革
本书收录了七篇当代中国思想访谈,受访者分别是钱理群、秦晖、许纪霖、于建嵘、袁庾华、陈明、高放。这七篇访谈自2009年起陆续发表于《思想》季刊。
- 国宝级思想家钱理群(2009)
- 追求社会公正与宪政民主的秦晖(2010)
- 反思富强崛起、呼唤文明崛起的许纪霖(2010)
- 研究底层维权抗争的于建嵘(2011)
- 非典型的毛左派袁庾华(2011)
- 倡议公民儒教的新儒家陈明(2012)
- 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放(2012)
各篇访谈概要
钱理群
钱理群先生是这个系列访谈中第一位受访者。钱先生在北大执教期间,以鲁迅和周作人研究著称。2002年退休后,接连出版《拒绝遗忘》、《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民间思想史钜著。他在访谈中指出,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共建政后,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一党专政模式,但始终迈不过一党专政这一门槛;今日中国的两极分化、生态破坏、精神伦理危机等,终须归结于一党专制和国家主义。此外,他强调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国民性批判的当代意义:“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以立人为中心,要更关注人的个体生命的成长、自由、发展。”“只要中国人心不变、国民性不变,再好的制度到中国来,也仍然行不通。”他呼吁大陆知识分子积极争取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在制度重建之外,还需要全面的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
早年,钱先生曾是文革的全程参与者,是造反到底的造反派。他后来对毛主义的反思批判,都同时也指向他自己。鲁迅是他最主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他立志继承“鲁迅的五四”,做为永远站在平民一边的“鲁迅左翼”。在今日大陆的左右光谱上,钱先生是一位难以归类的国宝级思想家。
秦晖
秦晖先生也曾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在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中,他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中,他是最早提出“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的论者,对邓小平南巡后的“权贵私有化”持坚定的批判立场。按他的陈述,南巡后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一种专制分家;在俄罗斯,正因为此种分家方式太不公正,引发寡头派和民粹派的恶斗,也才使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为可能。不公正的专制分家,为中国未来种下了危险因子。如果不想付出推倒重来的社会代价,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作为矫正正义)也就无可迴避。
秦先生强调,赞成福利国家,须以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作为前提。民主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关乎社会公正与公民基本权利。俾斯麦式威权体制下的福利,只是皇恩浩荡而已;在当前中国的专制体制下,福利更经常沦为一种负福利。因此,他阐发以“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作为宪政左派与宪政右派的共同底线。他申论:如果左派不为政府扩权,而是积极追问其责任;如果右派不为政府卸责,而是努力制约其权力;那麽,中国就会逐渐趋近于权责相符的宪政民主。
许纪霖
许纪霖先生把晚近的中国崛起界定为一种“富强的崛起”。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仅实现了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受到富强崛起的鼓舞,大陆出现了一波鬼鬼祟祟的国家主义政治神学。和昔日的德日法西斯相似,这是一种只有明确的反抗客体(即“西方”)却没有主体的抵抗。如果这类国家主义继续与集权体制、与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恐将把民族拖向无底深渊。唯有当国家理性受到现代启蒙理性的制约,并与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中国才可望实现文明的崛起,成为普世文明的领航者。
许先生不讳言,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大国地位,它势将崛起为对周边具支配力的帝国,而不仅是另一个民族国家而已。但徒具支配力的强权并不可欲,唯有引领普世文明的大国才能得到全球尊重。他指出,当前富强崛起的中国,只是一个自利性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再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在此种霍布斯式的秩序下,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更没有社会。中国之乱已经不是乱在表层,而是乱在心灵。沉疴已久,制度改革将只是治标的止血;当前中国危机是整体性的,非得从基础上重建社会、重建伦理不可。在此,他多方面呼应了钱理群先生的忧虑。
于建嵘
于建嵘先生长期研究底层中国的维权抗争,首创“刚性稳定”概念以界定维稳体制。近年来,由于他的“敢言”及其所依据的实证调查,他成为大陆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出于《思想》的访谈要求,于先生首度较为系统性地交代了他的学思历程和基本理念。他从幼年经验谈起,解释他为何主张“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社会得先保护个人的权利才会有公共的利益。”他对中国当前的农民和工人抗争,农会和工会问题,各种“群体性事件”及其动力等,有一套独特的分类和理解。
于先生指出,中共的核心考量并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基于此,大陆的稳定主要是以“是否影响共产党的政权稳定”为标准,这跟今日台湾非常不同。中共为了巩固政权,把一切可以疏导压力的管道都视为不稳定因素,这正是“刚性维稳”体制日新月异的根本原因。然而,他并不认为中共绝无可能改变,只是中共不会因为“理念”而改变,只会在强大的政治社会“压力”下改变。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他持审慎的乐观:“大陆会逐渐走向台湾的政治运作逻辑。”
袁庾华
在今日大陆的毛派或“毛左派”中,袁庾华先生是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初中后,他就到郑州肉联厂当工人,尔后成为河南省造反派的骨干。1995年后,他参与郑州沙龙的创建和经营。在访谈过程中,袁先生除了回顾他的造反派经历外,亦对毛泽东和毛时代多所肯定。然而,他几项主要的政治主张,却与主流的毛左派有所差异。当前以“乌有之乡”作为主要代表的大陆毛左派,尚未接受他“结合程序民主(含竞争的政党政治)和大民主”的倡议。他呼吁中国政府同时平反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和法轮功成员,并强调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是全世界底层人民奋斗出来的成果,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但时至今日,多数大陆左派仍视如此主张为汉奸“引狼入室”的诡计。
访谈中,我屡次打断袁先生,询问他的见解是否为今日大陆毛左派的主流意见,并请他阐发程序民主和大民主之不同,以及他何以主张两者应相互结合。他表示,他的民主思路与大陆底层毛派群众是相通的,只是部分毛左派尚未充分体认到结合程序民主之必要。值得一提的是,袁先生访谈在《思想》发表后,通过大陆网站的转载,在毛左派内部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论辩。
陈明
1980年代初,牟宗三先生曾力主“第五个现代化”,要求台湾当局推动民主转型。但在今日大陆,呼唤民主转型的新儒家几不可得。在大陆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中,陈明先生属于对自由民主有较多同情的一位。他在访谈中指出,台湾儒家之不谈“儒教”,是因为儒教在台湾的教化力量太大,所以不必这么谈。在大陆,儒门淡薄,社会基础薄弱,因此,大陆新儒家提倡儒教作为一种宗教。但他反对蒋庆、康晓光等论者“立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路线。他主张儒教在另外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发展“作为一个宗教的儒教”,为儒教徒提供更充实的生死灵魂论述;第二,要立志把儒教建构为“公民宗教”,为中华国族提供跨族群的认同铺垫。
陈先生表示,他不是文化民族论者或文化国家论者,也不是天下主义者。对外,他看重中国作为国际现实下的一个利益主体。对内,他认为在中华国族的构建过程中,儒教争取“公民宗教”的功能和地位是可能的,甚至必要。“公民儒教”如何与宪政民主的权利意识接轨,是他现阶段的努力目标。
高放
在这本访谈集中,最资深的受访者是高放先生。他出生于同盟会家庭,1946年入北大政治系后,转向了中共。1950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受推崇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首席专家。文革后,他率先对“个人崇拜”提出批判,并于1988年担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更不断呼吁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
高先生在访谈中表示,他不认为多党平等竞争目前是可行的,因为中共绝不会接受。按中国宪法,省长需由民选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故而,只要把宪法理顺,党政分开,中国就可以迈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现阶段尚不需要考虑到党外,但要让民主党派壮大,要实施共产党内的差额竞选。他指出:当前的“中国模式”是四不像,唯有清理掉两极分化的美国模式成分、严控思想言论的苏联模式成分、国营垄断的欧盟模式成分,才能真正实现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序言摘录
摘录一:中国现状(2013)
当代中国充满了难以调和的对比。它已经是世界强国之一,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它既无法管束自己官员的贪腐滥权,也尚未建立人民敢信任的统治秩序。它帮助许多人在一代之间从赤贫变成富有;但从饮食、交通、住房,到教育、医疗、退休养老,几亿人民必须每天地、无奈地、心力交瘁地保护自己,鑽营机会。它的宪法明言“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不过中国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中国农民没有农会,工农阶级在党内党外均说不上任何领导角色和政治意义。它的体制自许“具有中国特色”,不跟随既有的任何发展模式;不过除了维护党国官僚集团(以及周围的附庸)的独占地位之外,你很难说这套体制还相信什么、追求什么、还有什么理想与向往。
…………..
今天的中國強大到只舉得出「中國」這個符碼,其他的一切都有待摸索:這似乎是中國龐大身影所映照出的尷尬難局所在。
摘录二:知我者谓我心忧
在当下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与异议者也在关注同样的问题。他们亲身经历过几十年来的大小风暴,仍设法维持独立的心灵,缜密的思考,宽广的视野,以及对民间疾苦的悲悯情怀。钱理群先生选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作为他一本书的题名,多少形容了这批忧思者的自我定位。
………
受访者对于中国当前难局的来龙去脉、对于体制的沉疴、对于中国革命史的方向与病变、对于底层抗争与平民百姓的遭遇,皆有严肃、深入的理解,他们的分析与呼吁自有参考价值。
摘录三:大国崛起对人类的应有贡献
让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军事、经济的崛起,而能对人类做出更积极的贡献。所谓的“大国崛起”必须提出、体现某一套普世价值:
英国开创宪政与法治,法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美国倡导民有、民治、民享,甚至苏联也宣扬过“无阶级的社会”,彼时成为整个时代的向往所在,也织入了人类的共同文明史。(当然,这些大国崛起另有其黑暗的一面。)
另一种强调特殊性、对抗性的崛起,如德国的“以文化对抗文明”,或是如日本的“超克现代”,则带来了生灵涂炭、祸人祸己的后果。
摘录四:视野狭隘的国家主义
自美国陷入金融危机后,“中国即将统治世界”的预言、欲望或警语,更甚嚣尘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言犹在耳,但就在短短几年间,大陆内部强势兴起了一波视野狭隘的国家主义浪潮,不断吹捧“中国模式”的独特和美妙。
………
中国的崛起是不是能带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动力,在世界上推动人道与互助;是不是能够给十数亿境内以及周边社会的人民带来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是我们所关心的根本问题。